來源:中國核電信息網 發布日期:2014-08-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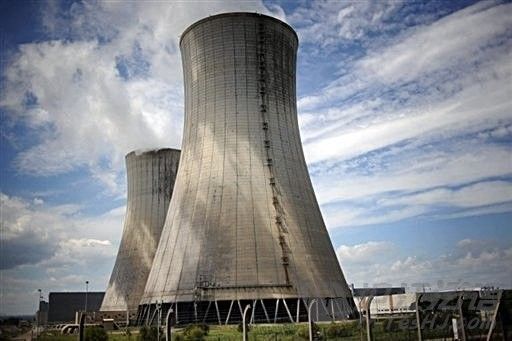
從歐洲整體環境看,德國所謂“棄核”實際上是虛幻的。再對比日本這樣四面環海的島國,棄核更加不現實,所以2014年日本政府通過的能源政策,將核電定位為“為能源供求結構穩定作出貢獻的重要基荷電源”,為核電重啟預留了空間。對中國而言,在發展可再生能源同時,決不能放緩核電的發展。
近10多年來,全世界各國都在大力發展風電、光伏,主要是出于能源價格、能源安全和低碳能源三方面的戰略考慮:1)常規化石能源(特別是石油)價格不斷上漲,光伏、風電等可再生新能源最終會成為質優價廉的能源;2)常規能源依賴進口,而且總有枯竭的一天,發展本國的可再生能源可保障能源安全;3)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因為可再生新能源是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清潔能源。目前世界上已經有近百個經濟體以強制性上網電價補貼(Feed-in Tariff)的政策措施予以大力扶持。到2013年底,全球風電總裝機已經達到318吉瓦(其中中國91.4吉瓦)、光電總裝機139吉瓦(其中中國19.9吉瓦)。
一、德國新能源(20.24, 0.06, 0.30%)政策面臨的困窘
德國,可謂是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典范。2011年6月,德國議會通過了關于能源轉型的議案,確定核電站將在2022年底前逐步關停,在未來40年內電力行業全面轉向可再生能源(包括水電)。到2014年7月德國光伏裝機達到37.4吉瓦、風電裝機達到34.6吉瓦,已經分別達到德國發電總裝機(175吉瓦)的21%、20%。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5月11日,這一天的中午時分,德國的光伏、風電出力高達當時負荷的74%;在2014年6月9日,僅光伏出力就超過負荷的50%,創造了歷史記錄。此外,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充裕,德國2013年出口電力達到314億千瓦時,比2012年大幅增長了36%。
但是,在這些被媒體廣為傳頌的亮麗數字背后,也有難以言說的隱憂和窘境。我們就以能源價格、能源安全和碳排放這三個指標對德國這些年來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實踐做一個評估,以此引出對中國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啟示。
首先,從能源價格的角度來看,風電、光伏的發展給德國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僅2014年一年,德國對風電、光伏的補貼支出就需要約300億歐元,如此高昂的補貼資金由消費者來承擔(“可再生能源附加費”0.053歐元/千瓦時)。德國民用電費已經從2000年的0.14歐元/千瓦時升至2013年的0.29歐元/千瓦時。此外,由于按照電力市場規定任何時刻風電、光伏都要優先上網吸納,而受到補貼的光伏、風電的可變成本是零,因而導致了電力市場平均成交價格大大降低,從2008年的平均0.095歐元/千瓦時降至2013年的平均0.037歐元/千瓦時。電力交易市場成交價格的低迷,使得德國主要電力企業利潤大大縮水,2010年以來其股市價格跌去45%左右。
第二,從能源安全的角度來看,由于風電、光伏屬于間歇性的電源,其裝機容量的大幅度增長擠壓了燃氣和抽水蓄能電廠的市場空間(燃氣發電2013年比2012年下降21%,而2012年比2011年下降17.8%),卻無法代替逐步關閉的核能電廠,因而能夠連續運行滿足基礎負荷的燃煤電廠填補了核電的空缺。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頁巖氣革命以來多余的煤炭產能在國際市場尋找出路,煤價處于近年來較低的水平,加之歐洲碳交易市場價格低迷,煤電也是財務狀況不佳的德國電力企業的首選。2013年德國煤炭消費為8100萬噸標準油,而當年煤炭產量為4300多萬噸標準油(比2003年下降了23%),煤炭對外依存度高達47%,高于2012年的43%。2013年德國核能發電量相當于2200萬噸標準油,未來數年內均需煤電來替代,但由于國內煤炭產量逐步下降,德國煤炭對外依存度勢必還要相應增長。
第三,從溫室氣體排放的角度來看,德國在2011年以前二氧化碳排放是不斷下降的。按照德國的減排承諾,德國應在2020年實現相對1990年減排40%。德國至2011年已經實現減排25%左右,需要在未來年份中每年實現減排2%左右才能實現減排承諾。然而,在2012年燃煤發電比2011年大幅增長16.8%的情況下,2013年德國煤電比2012年又增長了6.5%,達到總發電量的53%,煤電比例創1990年以來的歷史新高。因此,德國二氧化碳排放的趨勢自2012年起發生逆轉,連續兩年碳排放增長超過2%。如前所述,隨著德國核電站的逐步關停,未來幾年內煤電比例及相應的碳排放還會進一步提高,所以德國將難以實現其2020年減排40%的承諾。
綜上所述,德國以光伏、風電發展為標志的能源轉型政策面臨困窘:1)財務負擔日益沉重;2)能源對外依存度增加;3)二氧化碳排放不降反升。也就是說,德國能源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這些結果與發展可再生新能源的初衷背道而馳。德國在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值得其他國家,尤其是正在大力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中國參考和借鑒。
二、以德為鑒,中國應加大核電發展,走向“核諧”社會
首先,我們應該明確可再生能源的定位,不能要求光伏、風電承擔能源技術經濟體系中“不可承受之重”。雖然德國光伏、風電裝機已經分別達到發電總裝機容量的21%、20%,但由于光伏和風電屬于間歇性電源,2013年光伏、風電在德國發電總量中分別占6.2%、9.8%,總計約合16%。光伏、風電在德國總發電量中能夠達到這樣的比例,沒有一體化的歐洲大電網作為市場依托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國大陸幅員廣袤,類似歐洲大陸,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也應該依托一體化的堅強智能電網,才能真正保證光伏、風電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換句話說,中國在部分省份的光伏、風電發電比例依托一體化的國家堅強智能電網可以達到較高的比例,但是對于國家整體而言,光伏、風電在總發電量的比例難以超過10%,折算在一次能源供應中的比例不足5%,只能是一種補充,難以承擔能源安全的重擔。
第二,在目前技術經濟條件下,發展光伏、風電等可再生能源不能沒有政策補貼,但是決策者應該慎重考慮補貼資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不應加重普通老百姓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經濟負擔。以德國的光伏發電為例,40%左右的光伏是分布式的,也就是安裝在建筑屋頂上的光伏發電裝置。然而,能夠有足夠大的屋頂安裝光伏發電裝置的大多是相對富有的機構和居民,而對于這些光伏裝置補貼的資金來自所有用電戶,包括收入較低的群體(在德國有690萬戶居民被稱為“能源貧困戶”,其收入的10%用于能源支出),政府卻對4000多家能源密集型企業免征可再生能源附加稅。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說,德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伴隨著資金從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流動的過程。這樣的可再生能源補貼不僅不公正,也難以持續。汲取德國的經驗,我國應考慮對“耗電小戶”(僅用于基本生活用電的居民)適當減免可再生能源附加費,而對各類“耗電大戶”(包括能源密集型企業、商家和個人)增收可再生能源附加費,不僅保障公平性,還可進一步倒逼這些耗電大戶更自覺地采取節能措施。
第三,由于光伏、風電的間歇性技術特征,不能取代被逐步關停的核電廠,使煤電在德國成為必然選擇,造成二氧化碳排放不降反升。需要指出的是,德國位于歐洲大陸中心,與周圍所有9個鄰國電力并網。雖然自身逐步棄核,卻隨時輸入法國、瑞士等國的核電來滿足基本負荷,否則煤電的需求還會更高。從歐洲整體角度看,德國的所謂“棄核”,實際上是虛幻的。對比之下,像日本這樣四面環海的島國,棄核更是不現實的。所以2014年日本政府通過的能源政策,將核電定位為“為能源供求結構穩定作出貢獻的重要基荷電源”,為核電重啟預留了空間。對中國而言,我們不但面對國際上越來越大的減排壓力,更要解決威脅人民健康的嚴重霧霾問題,所以在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時,決不能放緩核電的發展,否則將無法控制乃至減少煤電的規模,減排和治霾都將成為空話。長遠來說,能源結構中煤炭、水電、核電、天然氣、風電、光伏“一個都不能少”,其中最關鍵的還是核電。隨著核電技術安全性的提高,要逐步提高百姓對核電的信心,走向“核諧”的社會,將是我們國家保障安全、清潔、經濟的能源供應的必由之路。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
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法規,尊重網上道德,承擔一切因您的行為而直接或間接引起的法律責任。
中國核電信息網擁有管理留言的一切權利。
您在中國核電信息網留言板發表的言論,中國核電信息網有權在網站內轉載或引用。
中國核電信息網留言板管理人員有權保留或刪除其管轄留言中的任意內容。
如您對管理有意見請用 意見反饋 向網站管理員反映。
 同類 國內核訊
同類 國內核訊 ©2006-2028 中國核電信息網 版權所有 服務郵箱:chinahedian@163.com 電話:13263307125 QQ:526298284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